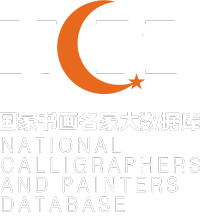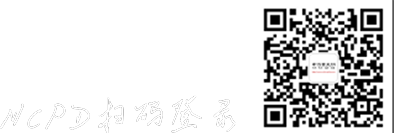作为一位漫画家,他的漫画是“大漫画”;作为一位设计师,他的设计体现着博大的文化胸怀;作为一位美术教育家,他要构建一个“大美术”的教育框架。而作为一位大美术家,他朴素、厚重、不张扬、不矫饰。他,就是张仃先生。
文化名人王鲁湘把自己形容成喜欢寻觅“野食”的“杂食动物”;而张仃也是一位涉猎众多门类的大美术家。也许正是这一共同的特质,让他们成为多年忘年交的好友,更让王鲁湘能深入地了解张仃、理解张仃、解读张仃。本期王鲁湘为我刊撰写了特稿,带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去追忆这位大美术家。
人称张仃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这个“大”字,当然包含有“大师”、“大家”的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取其“宏大”、“宽博”的意思。
20世纪中国的美术,有许多大师和大家,对他们的称谓往往是“油画大师”、“中国画大师”、“山水画大师”、“人物画大师”、“风景画大师”等等,也就是说,大师往往是在一个门类或一个画种上术业专攻,卓然成家,居于这个门类或这个画种艺术成就的巅峰,因而被谓为大师。
但是张仃似乎与此不同。他涉猎的艺术门类和画种太多,而且不是一般地浅尝辄止,或是客串玩票,一旦这个门类或画种他涉猎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都会成为这个门类或画种的代表性画家,甚至成为领军人物。我们稍微罗列一下:
20世纪30年代,不到20岁的张仃闯入漫画界的时候,张光宇、叶浅予这些中国漫画界执牛耳者都惊呼“发现了一座金矿”。张仃很快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一员漫画猛将。他的漫画没有市井气,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小情小调,甚至没有幽默,只有愤怒,只有抗争,只有揭露,只有攻击。他的漫画不是给人性的弱点挠痒,而是对人类的罪恶进行炮轰,他炮轰的对象是法西斯、独裁者、战争狂、掠食者、卖国贼。他的漫画主题宏大,风格刚猛,表现出同上海滩漫画很不一样的大气魄、大格调、大手笔、大关怀。他的漫画是“大漫画”。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亮相,亟需形象设计与包装。从开国大典、建国邮票、建国瓷、一直到各种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张仃参与其中,不是作为组织者、领导者,就是作为总设计师。他所倡导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成为中国装饰设计学派的指导思想。在民族风格中,张仃又特别提倡从民间艺术、草根艺术中吸取营养。他自己的装饰设计,特别注重民间艺术清新之风、文人艺术蕴藉之雅、宫廷艺术堂皇之颂三种传统的协调融合,加上时代要求与国际视野,形成刚健、清新、庄重、典雅的中国气派。1956年的巴黎博览会中国馆,从馆体建筑设计到展陈空间的布置,就是一件风雅颂高度融合的大艺术品。馆体是宫殿建筑—颂,内庭是文士园林—雅,陈设中有大量中国各地区的民间工艺精品—风。难怪中国馆会在博览会中格外抢眼,赢得巴黎人民的青睐,一位巴黎富豪甚至提出整体收藏中国馆的要求。张仃的装饰设计风格以及由他倡导并领导的中国装饰设计学派的美学主张也是“大”的,大国气象,广土众民,必须融合太多的资源,没有博大的文化胸怀与艺术涵摄力,不足以担当此重任。历史选择张仃,是有理由的。
作为美术教育家的张仃,他要构建的是一个“大美术”的教育框架。张仃自己是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美术训练的。他的美术启蒙来自于童年的民间社会。由于重视教化,中国民间社会的“像教”很发达。张仃的童年是在一个很传统的殷实的家庭,在乡下生活中,红白喜事、节庆庙会,都有民间艺术掺杂其中,红红绿绿,煞是好看。张仃年轻时初见毕加索作品的珂罗版就喜欢异常,正是看到了毕加索艺术同他童年记忆中的中国民间艺术的相似性,那种表现的大胆、热烈、夸张、变形,及由此带来的无法言说的兴奋,使张仃意识到学院美术的严重弊端就是扼杀了这股原始生命力。所以当他有权力主持一家国家级美术院校时,他就把面人汤、泥人张、皮影陆请进了学院,给他们成立工作室,给他们配助手。在他主持之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课堂延伸到石窟、寺庙、民间、乡下及边陲少数民族地区,老师扩展至各种工匠、艺人包括大妈、大婶,学生要成为多面手,衣、食、住、行、用,各个生活、生产领域,都要进得去,拿得起,向生活学习艺术,亦用艺术美化生活。故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吃“百家饭”长大,艺术上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张仃不止一次同我说过,大师不是院校培养的,大师都是生活培养的,社会培养的。虽然从事了大半辈子的艺术教育,但张仃一直对艺术院校的教育效果持怀疑态度,所以他总是把院校的围墙打开,让学生们尽可能多地到社会上去,到生活中去。他希望艺术教育的路子更宽一些,更野一些,更自由一些。我想,这其实就是他自己成长的路子。
很多艺术大师都师承某某,或毕业于某某著名艺术院校。张仃是个例外。他无师自通,一生中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他私淑的老师却多得惊人,小时候在乡下临摹过水陆法会的地狱图,学习过报刊上的摩登广告;在北平美专,跟一些京城的国画先生学习过水墨山水、花鸟;又通过印刷品认真学习过墨西哥的漫画和壁画;同张光宇结识后,对其抒情性很强、特别讲究线条造型的唯美画风很崇拜,这种画风在《哪吒闹海》动画片和同名的壁画中有很好的表现。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同李可染一起搞中国山水画革新,拜黄宾虹和齐白石为师,在笔墨上很是下过一番工夫。由于有出国办展览的特殊机遇,他有机会在欧洲的博物馆看到大量经典原作,也有机会带回一些现代派画家的画册,他用彩墨很认真地临摹过毕加索、莫狄里埃尼、勃洛克、鲁奥的作品。这方面的学习,对于他创立“毕加索城隍庙”的装饰绘画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收集大量的民间木版年画、绣片、玩具、剪纸、皮影,潜移默化地从中吸取造型意识、色彩表现手法;他考察古代岩画,从岩画和汉画像石中体会原始的造型意趣及其粗犷神致;他甚至还向儿童画学习,收藏了一些天才儿童的作品,还临摹儿童画。当然,他也向古代的大师和今天的大师学习,他意临过赵伯驹、倪云林、石、吴昌硕、黄宾虹、朱屺瞻、黄秋园、李可染、陆俨少,他甚至还意临过学生的作品。他的学习态度是很博大的。
张仃说自己是个“杂食动物”。韩羽也曾一语双关地说过张仃“有一个农民一样强健的胃”。不挑食,不偏食,什么都吃得下,什么都吃得香,什么都能消化,变成营养。在生活中,张仃一日三餐的安排就很有文化上的象征意味。他早上起来,烤两片面包抹上黄油,冲一杯咖啡,煮两个七成熟的鸡蛋。这种吃法同欧洲人一样,他的早餐是西化的。中餐吃几个小菜,荤素搭配,一小碗米饭,这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晚餐喝杂粮粥,一点咸菜,这跟中国农民差不多。他喜欢吃上等的外国巧克力,喝上等的中国绿茶,洋酒、白酒、红酒、啤酒都喝,但都是适量。抽烟斗,烟丝都是进口的,有浓浓的酒香味。衣服喜欢穿那种摸上去有质感的面料,或者是意大利花呢,或者是中国土布。家里用的碗一律来自民间,一些来自欧洲民间,一些来自中国民间。太精细、太贵族的东西他不要。晚年他在北京门头沟盖了座石头房,装修时明确提出三不要:不要宫廷气,不要贵族气,不要地主气。最好是北欧民居和中国民居的结合。朴素、大器、厚重、有质感、不张扬、不矫饰,这是张仃对家居设计的要求,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对自己做人的要求,也是他对艺术的要求。
看上去,张仃的生活、艺术上都非常随和与包容;实际上,他在品味上极其苛刻。名气再大、价钱再贵的东西,只要不入他的法眼,白送给他也不要。我亲眼见过多次:他把别人当宝贝一样送给他的东西(有些是很昂贵的工艺品或古董)眼睛眨都不眨就转手送人了。所以他虽然一直担任工艺美术学会的领导,但他家里却很少有别人视若拱璧的古董或工艺品,因为流行的趣味要不就是宫廷气,要不就是贵族气,要不就是地主气,而这三气都是他不能让进家门的。
张仃晚年把自己收缩在山水画这一领域内,有些人替他惋惜。在我看来,无论打得多开的艺术家或学问家,最后一定会有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所谓由博入约,由益反损,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山水是“宇中之大物”,天地之间,山水可以赐神,可以卧游,可以极风云之变态,也可以寄故园之思,养丘园之志,这是中国人与天地合其德、与阴阳合其神、与四时合其序的最理想的寄托物。张仃晚年皈依大自然,与造化为友,是将一生大抱负升华的最好归宿。幸亏张仃晚年对焦墨山水画的执著,我们才可以在山水画这个伟大传统的长河中,又看到一股清气贯注,又看到一朵浪花涌起。张仃把这个伟大时代的禀赋通过一种个人的方式,化入了他的山水画,朴素、大器、厚重、有质感,是大山水、大气象、大格局、大承担。张仃之成为“大美术家”,其大山水是重要成就之一。
来源:《中国美术》